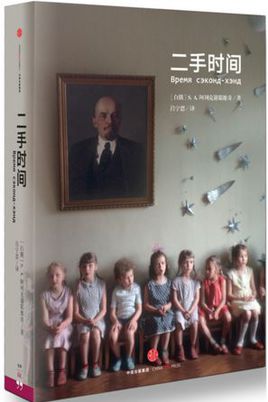二手时间(节选)
陈蔚文
1.
这条街巷——我从不知这城有这么条街巷!它毗临这座省会城市最繁华的商业街中段,从租金高昂的商业街折进这条支路,再从支路拐进巷陌——密密匝匝的小店,黯旧老平房,“布满肋骨似的椽子、梁和桁梁”,四处吊挂的衣物……巷边炉上支着乌黯铁锅(锅龄少说二十年往上),古老劈柴升腾着火焰,近旁一伙店主嘻嘻哈哈地斗牌扯闲。
城市的盲肠,注满阴影与褶皱。青灰的柴烟悬浮半空,挨挤小店壅满衣物,它们整麻袋(有时是更庞大的打货袋!)被运进巷,来不及拆包的堆在墙角,本来逼仄的面积变得愈困狭。
勤快些的店主支块板熨烫,白汽升腾,激起复杂气味:难以剥脱的,已锲进面料分子中的体味与高温蒸汽的搏斗,时间深处涌出的霉潮。
随远亲H办事,比预期结束得早,办事地点就在这副街巷的近旁,她领我走进,神情像进入珍宝之地。刚才还平正的脸色像饥兽嗅到猎物的血,骤然抖擞!在巷深处一家小店,H拨拉着架上衣物,挑中一件,脱去外套后熟练往身上——只穿内衣的身体——哗地一套,我喉头一紧,仿佛不祥的,令人不安的冰凉正黏紧她丰腴肉体!
试衣者不少,多数如H姿态熟练。新客有些游移,吞吐着往身上套,在狭窄镜中打量,与店主侃价,交钱,匆匆离去。
这些衣物,没人问出处哪里,买的和卖的,心照不宣。若知道自己买下的这件正附着某些病菌与死亡气息,会否使买者惊怵?也许顾客都像H般怀着模糊侥幸:是健康的生者因喜新厌旧而淘汰,仅此而已!
店内衣物胡乱堆码,古旧与流行混杂,甚至还有堆在巷子旮旯里的围巾手套胸罩、各色连裤袜——有女人当场把袜子套上大腿以观效果:如此贴身私密的拥抱,像借用了袜子原主人的皮肤。
这些衣物,它们如何流转于此,无需答案,来此地的顾客先就摒弃了这些纠结。低廉得让人蠢蠢欲动的价钱才是关键。
没有戒律,没有禁忌,敞裸的实用主义的“唯物”。
不少店子兼住家,外屋售衣,里屋住人。一魁壮男子在昏暗里屋喝酒,餐桌上一盘吃得狼藉的鱼,鱼味儿从满屋复杂气味中挣扎而出。我匆忙走到屋外,在门外等H。洒在巷道的正午阳光比照在其他任何地方的更宝贵!它不仅意味着杀菌,还意味着当下的时间:巷间此刻被阳光照拂的时间仿佛才是活生生的,流动的,新鲜的!而屋内——即使有个魁壮身躯在那,依然有叠加的阴影,像布鲁诺·舒尔茨在《鳄鱼街》中描述的:
“被其他人磨损过了,那是一种千疮百孔,像张筛子般褴褛不堪的时间。不用奇怪,这是所谓反刍过的时间——请原谅我这样说:那是一种二手时间……”
2.
难以克服的心理禁忌令我觉得那满屋堆积的衣物,无论怎样清洗消毒,都坚执地吸附前任主人永不弥散的体味、声容乃至喘息——高潮的,痛苦的……人类在各种情境下可能发出的声响:床或病榻。
这些体味,若是《香水》中的主人公格雷诺耶在场,他闭上眼就能凭着出色的鼻子,从气味中提炼、还原各种人形:衣物的前主人。年轻、中年或老年,削瘦或胖大,高或矮,平庸或夸张,衰颓或艳丽。这样的联想令巷中兀自升起许多沉默的幽灵,他们四处走动,寻找属于自己的衣物,找到了,与衣服合为一体。
好吧,即使格雷诺耶不在场,凭着其他穿着痕迹也能导引出一些信息。松脱的袖扣,烟烫的小破洞,断落的拉链头,裙腰爆绽的线……
衣物对应着形色身影:物与人发生联结后的被塑造。
H从一件大衣口袋摸出枚有锈迹的发夹,淡紫——它曾别在什么样的女人鬓间?
走在前头的H,黑呢外套, 深V领毛衫(乳峰耸动),包臀短裤(比她腰腹小一个尺码,拉链需吸气方可提上),这一身皆出自这些弯绕串联的小店!衣物来自何方不重要。不管水洗标上印着 Korea或Japan,可能都是Madein China,从中国流水线出发,绕了个圈,它们又回到产地。
H下个目标是挑顶帽子,在一家拄拐的胖女人的店内,有整整几麻袋各式帽子!这些帽子还依稀保持着原佩戴者头部的某种形态。H扒拉出一顶贝蕾帽和一顶深紫毛线帽,可要价超出她预计。瘸腿女店主以与体形同样硕大的固执毫不退让,“就这价!”她坚定地晃晃拐。
H悻悻离开,好在接下去她另有斩获。她买下件极短的绿上装,绿得像蚂蚱迸溅的体液。衣服主人多半也是个胸围蓬勃,鲜衣怒马的女人?不然扛不住这绿!店内两个女人正发生口角,为一条黑色吊带裙,活像于坚的那句诗,“两位顾客在争夺Kenzo裙/扯裂腰围/仿佛那就是失踪多年的美丽青春”。
拐弯处的小店,说话大舌头的女店主热情招呼H进来看,边兴奋展示自己昨夜两点才从发廊出炉的新发型。挑染的紫红。“六百块!从没烫过这么贵的头,我老公说我疯了!不是快回乡下过年,我也不舍得……”可以想见,这丛凌乱紫红在她的乡下会引发多少眼光。她的狭小店内挂满各色白衫,白衬衫白裙子白背心,店内像个微型灵堂。H对白色不感兴趣,但对女店主的新发型表示了赞扬,接着去隔壁店看水货表。浪琴、欧米茄、Coach,店里播着《绿岛小夜曲》,留八字胡的矮个店主据说是交谊舞迷,穿曳地喇叭裤(白色!),像从舞场直接来了店里。
3.
自从H无意中闯进这爿街巷,有如吸食大麻。职业主妇的她对衣物和时髦有近乎热病的追逐,但她同时深具一名主妇对价钱的算计——现在,这爿街巷为她在时髦与钱包间提供了最大可能的平衡!
她隔三差五来,以一名时间富裕者的耐心逐件淘选。她来得如此频繁,以致有店主以为她打货。若有阵没来,她焦灼难安,担心有适合衣物旁落他人。那每一件,都是惟一的一件!
在这里她不仅实践着对捯饬的狂热,还兼顾社交。她在这认识了一个年轻女人I,H说她头回见I时,I正推辆童车在巷内游逛,气定神闲,像有闲太太晃荡在“燕莎”或“久光”。
H立刻被震了,被这个孩子才几个月身材已如此骨感的女人。她们同时进了家鞋店,I取下一双涂鸦风格的板鞋试穿,那双H看不懂的花哩胡哨的高帮板鞋套在I伶仃的脚踝立刻有了让她看懂的意思——潮!
H以她惯来的自来熟劲儿和I搭话,很快成了朋友。
“她看去很大牌!”这是H对女性美最高的赞扬。H的潜台词是:“甭小瞧这儿,其实卧虎藏龙!”
证明此地有人物的还有其他人证。
H到一家店前,小声介绍店主前任身份是家企业的会计,当然这非重点,重点是她身边另位头发花白的女人,“喏,那个戴眼镜的”,H搡我一下。一位眼镜后透着犀利目光的女人正与店主聊天抽烟,她们看上去像对历经沧桑的老闺蜜,有旁人介入不了的气氛。H说那个眼镜女人在国外待过若干年,是名钢琴教师,“她的衣服还有老公孩子的全在这儿买的!”——在国外待过若干年及“钢琴教师”身份成为H在此购衣“不掉份”的有力保证。
H在这店里相中一件镶拼的人造皮草背心,还价,店主一文不少,H不死心地嘟哝,“旧的还这价?”
“旧的?什么不是旧的?”穿大摆花裙的钢琴女教师吐了口烟轻蔑地答。
“什么不是旧的?”——这仿佛是哲学层面的追问,是的,世界本是旧的,内部为无数损耗充满:在这巨大的旧中,有什么能避免成为旧?在时间氧化剂里,所有事物不是已然旧,便是正去向“旧”的途中。
一切新始自旧!新的肉体诞生于旧的肉体,新的衣物始自旧的浆料,新的时光缘自旧的岁月,新的社稷脱胎于旧的江山……新旧相互转化,相互依存!通常,旧指丧失了存在的必然性(文物除外)、日趋灭亡的事物。然而对这些二手衣物,“旧”只是对某个人失去了存在必然,却会在下个主人身上重获必然。
“一些相互作用是在并不真正相识的人中间发生的”——这也正像为二手衣物下的定义:近到发肤的联结发生在陌生者当中。
二手房二手车二手家具……在市场定律中,“二手”意味损耗、折旧、处理,包括“二手人”(通常指女性。在搜索网页输入“二手人”,跳出的第一条是“二手女人”的词条)。这些二手的流通是被允许的合理,对资源的物尽其用,它们以环保的名义进入市场,促进着消费端的活跃。
二手衣物是种特殊的“旧”,离肉体太近使它们具有无法与前主人真正分离的性质。而前任主人,他们的身份病史习性都是未知的断层。
“单单是一般居民的旧衣物,哪能有这么稳定的货源?废品回收站、垃圾填埋场、洋垃圾,甚至贼赃和太平间等,都成为了二手衣物的来源。小贩们按斤收购……”来自《广州日报》的一则报道。灰濛的旧。危险的旧。浑浊的旧。深不可测的旧。
他人之“旧”,为何令人躲闪,疑虑?“旧”中有不可见的习性、过往,有不可知的纠葛与叵测,旧是“陌生化灵魂”的符码。“旧”中潜藏的细菌兴许会发作成一场病毒。旧,折射着“他人即地狱”。
与己有关的“旧”不同,它们指向时光,信物,指向一些虚无蒸发完后的晶体。
旧的旋律,旧的车票,旧的玛德莱娜点心,这些旧足有与记忆会合的扩张力。
五一节在天津,一位好友母亲说起病逝不久的老伴是极爱干净的人,连块手帕都洗得雪白,再旧的裤子都要折出裤缝。老太太打开衣橱,摸挲着那些衣物,哽噎,“说走就走了!脑梗,就几分钟,谁想到呢……我一人多孤单哪!”老太太颤抖着,流着泪捏捏我的手。
这一橱衣物是要伴她终老的,这些悬挂齐整的衣物,每一件,都是老先生的化身。
另些旧物却成把柄,成为在喉之鲠。
当一段关系由亲变疏,成为对立,旧物的温泽瞬变寒光!“旧”不一定意味已完成,意味保全,是的——譬如影像、信笺……这些情意绵绵的信物亦有可能成箭矢之毒。
几年前,楼下一对夫妇离异,为财产分配的“公允”,当医生的丈夫竟将床板一锯为二!那曾承载缱绻体温的床板,坦露着“旧”遭遇断裂后的冷酷。
4.
H从“很大牌”的I那里还学到一个词“古着”。这个时尚业的术语被她们当作了购“二手衣”的又一个理由。H说,明星都喜欢“古着”呢!
“古着不是二手衣的概念,而是真正有年代的而现在已经不生产的东西,这些服饰无论使用的面料,细节的剪裁甚至用途都是当时那个时代的缩影,所以有着特殊的价值。”
复古的,经典的,主要售卖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服饰,这才是“古着”与“洋垃圾”之分!H和“很大牌”的I显然混淆了二者含义。或者说,任何理由于她们并不重要,从廉价里淘流行才是关键 。
H拎了堆斩获品,边走边抱怨,这里衣服越来越贵了,这些店主拿它们当新的卖呢!
“不过,”她小声嘀咕,“和外头比,这里够便宜!”
正是“便宜”使她欲罢不能。她在一家店一气买下五六件毛衣,这些毛衣,价廉大过物美,但她为每件都找到理由,“咖啡这件式样挺潮,蓝色中袖可春秋穿,米色可做打底衫,玫红……嗯,颜色够亮。”
还有N件吊带内衣及睡裙。一件蓝缎闪光低胸裙是H最得意的,虽然她要深吸口气才能将拉链提上!而且也没有可穿它的场合,但那有什么关系?她把它穿去小餐馆、麻将桌边、夜宵摊上,在这些她生活的主场,裙子受到朋友赞美(他们更有可能赞美的是H的D罩杯),对女友们的询价H含糊其辞,对衣物出处守口如瓶。
这爿灰茬茬的小店圆了她华丽丽的梦!
H的衣橱在“便宜”中迅速膨胀——这爿街巷,它还有个名字应叫作“欲望街”!它是如何怂恿了H内心对“物”的汹涌欲望啊。从最初的胡乱淘款式,H渐转向兼顾面料,在交了些学费后,她的出手准确率明显提高了。她的标准现在是“看去大牌或体面的衣物”,尽管,这些衣物并没使H成为她期望中比如今更“大牌”的女人。那些衣物,只是数量的平行叠加,并未构成一处台阶供H再站高一步。在她俗碌的主妇生涯,在她有限而单一维度的交际圈内,这些衣物顶多为她屡次孟浪的艳遇提供些助力而已!她的购衣关键词:低胸裙露背装豹纹衫打底裤纱裙(与网购广告页弹出的流行同步),在不同场合让男人眼睛发光。但不管艳遇几何,H仍在她的生活框架里。那些滋扰她的男人,同质不同形,揣着一色念头,发出同样急切信号,动着同样的手脚……
廉价与大牌,这原本完全不构成对称的事物,在此地,对H有了实现可能。她在廉价中翻找着体面。假若眼光够利,运气够好,的确能淘选出几件符合H购买要求的衣物。从乡村来省城打工的H,17岁认识了家在本城的丈夫,同居两年后结婚,生子,全职主妇。在她身上已看不出多少老家乡镇的痕迹。每年春节,H光鲜还乡,与她关系糟糕的丈夫一年只这一次要求配合,开车同回,住上一两晚,他先返城,H留下继续接受邻里羡慕。背地,她每天打电话给丈夫,急切徒劳地,掌握他的动向……
比起家中姐妹,H是唯一嫁入城市安家的一位。她努力保持战果,即使丈夫有了外遇,即使夫家亲朋并不拿她当碟菜,甚至觉得丈夫出轨是她为妻不当——你若有吸引力,丈夫怎么会出轨?!H的胸围够大了,吸引力的问题出在哪?H对衣着更孜孜以求,但她置装经费有限。这爿街巷的出现,有如神迹,再没有比“二手”更贴心的语词!
对H,“旧”毫无障碍,作为对曾经匮乏的补偿,“物”的占有胜过一切。耽美而算计的H迎来了自己的时装新纪元,像当年她取得城市户口,改变身份一样。她的购物欲被挑逗得近乎强迫症的癫狂!她认为女性魅力皆由肉体出发,而肉体少不了光鲜行头(正合乎消费工业时代的伦理)。
喷上从艳遇对象那里索获的香水,H在邻居、老家亲朋、儿子的老师及同学妈妈们面前,扮演着衣食优裕的时髦主妇形象。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6-7-21 21:08:14 [只看该作者]
Post By:2016-7-21 21:08:14 [只看该作者]
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6-7-21 21:09:28 [只看该作者]
Post By:2016-7-21 21:09:28 [只看该作者]
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6-7-21 21:10:32 [只看该作者]
Post By:2016-7-21 21:10:32 [只看该作者]
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6-7-21 21:13:04 [只看该作者]
Post By:2016-7-21 21:13:04 [只看该作者]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6-7-25 6:08:56 [只看该作者]
Post By:2016-7-25 6:08:56 [只看该作者]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6-7-25 6:09:16 [只看该作者]
Post By:2016-7-25 6:09:16 [只看该作者]




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:33.jpg
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:33.jpg